来源: 环球财经 发布日期:2014-12-23
导语:伊朗核工业的发展史,反映出“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与“防止核能被用来制造武器”这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互相冲突,一旦遇到国际政治与国家利益的纷争纠葛时,往往乱作一团,进而造成了伊朗核问题“久谈无果”的复杂局面。
距离人类上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随着二战中广岛与长崎的核爆阴云散去,核能在世人眼中,不仅是谈之色变的杀人武器,更成为重要的新型能源,有可能将为传统能源的短缺和污染问题引领出路。在打着“能源短缺”旗号发展核能的国际浪潮中,有一个能源显然“不短缺”的国家,那就是石油储量世界第三、天然气储量第二的海湾国家伊朗。
伊朗核问题有许多特殊之处,首先在于它作为一个海湾产油国,却搭上了石油危机后国际核电大发展的顺风车,背后折射出核技术扩散的复杂历史;其次,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的首批缔约国之一,早在1968年就签署了这一条约,这使伊朗核问题迥异于未签署条约的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谈判,不但关乎伊朗核工业的“合法性”,更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及《核不扩散条约》所搭建的“和平利用核能”框架的一次考验。195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之时,人们自信可以将民用核能与核武器区分开,同时实现“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与“防止核能被用来制造武器”这两个目标。然而伊朗核工业的发展史,反映出这两个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互相冲突,民用与军用核能之间的“防火墙”在理论上可行,实际中遇到国际政治与国家利益的纷争纠葛,却往往乱作一团,进而造成了伊朗核问题“久谈无果”的复杂局面。
1954年:核扩散元年
【1953年底,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开启了“核扩散”大门。除了政治目的外,另一原因是在核工业投入巨资的美国军工巨头们需要将成果变现】
1945年,美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研发出核武器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将核武器运用于实战的国家。毁灭性爆炸和放射性烟尘摧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垂死反抗,也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力量如果被不负责任的人们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从那时起,控制、削减乃至消灭核武器的呼声就不曾停止。大国之间开始谋求建立一种国际性准则。1946年6月14日,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代表、发家于华尔街的投机大师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率先提出了一个原子能管制计划,史称“巴鲁克计划”。要求设立原子能发展总署,管制原子能的一切发展和利用行为,在确立有效管制后,停止核武器生产,并销毁一切现存核武器。
巴鲁克计划“看上去很美好”,也得到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同意,但因苏联的强烈抵制而流产。苏联反对的原因一目了然:该计划把“销毁现存核武器”放在最后一步,并没有设立时间表,这意味着当时惟一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可趁机一统全球。苏联方面也提出了一个计划:要求签署国际公约后立刻销毁全部核武器。美国自然不会同意,国际社会建立核发展框架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不了了之。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原子能势力格局出现变化。然而,正如许多历史事件后的舆论争夺一样,率先报道这个消息的是美国媒体。在核能发展的舆论战上,美国依然占据主动。1953年12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和平利用核能”(Atoms for Peace)演讲,彰显了美国所谓“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表示愿意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以打破“令人恐惧的核困局”。“美国很愿意参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项目,并为之提供帮助。”艾森豪威尔表示。
“和平利用核能”演讲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它经过总统顾问们的用心雕琢,词句精美、鼓舞人心,成了许多英文演讲学习课程的范本。更重要的是,它将“民用核能”的概念推上历史舞台。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其实打破了盟友间的承诺: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加拿大签订《魁北克协定》,规定英美之间共享核技术相关信息,并严格保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原子能是大国的军事秘密,民间对其知之甚少。艾森豪威尔通过演讲昭告天下,美国研究核能是为了“造福人类”,其他国家可以“不劳而获”地共享成果——只要纳入美国的政治框架。
除了政治目的外,促成艾森豪威尔演讲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核工业投入巨资的美国军工巨头们需要将成果变现。1954年,美国对1946年通过的《核能法》(Atomic Energy Act)进行了修正,允许核技术的私有化和商业化,并允许与国外公司合作进行原料和技术出口,从而吹响了全球核工业的号角。苏联不甘示弱,也开始通过输出核技术拉拢盟友。美国人在巴基斯坦修建核反应堆,苏联人则把核技术提供给利比亚;属于苏联阵营、但也被美国拉拢的罗马尼亚则有了两座核反应堆:美国人修了一座,苏联人修了一座。
这时,一个美国人原本并不熟悉的海湾国家闯进了这场博弈,这就是伊朗。对于美国而言,伊朗一度是其核工业框架的重要棋子;对于伊朗而言,则在核能博弈中看到了国家崛起的希望。
美国核战略中伊朗的角色
【遥想当年,伊朗的核项目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的。然而,美国人主导的核不扩散体系存在先天不足,“限制军用”与“推广民用”之间的防火墙效果十分有限】
二战结束之前,伊朗与美国既无历史恩怨,也无深入合作。这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位于海陆交通要道,又富于油气资源,因此遭到欧洲列强的多次瓜分,沦为半殖民地。20世纪初,伊朗被英国和沙俄交替占领,积怨颇深。直到下级军官出身的老巴列维国王礼萨·汗(1878~1944)推翻旧王朝取得政权,以及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19~1980)当政期间,伊朗才在新旧国际格局的交替中获得机遇。为了在英国与苏联的势力夹缝中谋求独立,伊朗开始主动向“第三方”美国靠拢。
1953年美英情报部门联手推翻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1882~1967)的行动,“主谋”是英国军情六处,起因是维护英国石油公司(BP)在伊朗的利益。虽然这段“黑历史”经常被归咎于美国中情局,但其实更多是英国殖民时代的后遗症。美国的中东策略从一开始就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思路不同,金融、经济制度和全球化产业链的构建逐渐成为重点。具体在核工业领域,伊朗被西方视为“民用核能市场化”的标杆,美国想把伊朗纳入艾森豪威尔讲话中设想的“和平核能”体系内,从而在海湾地区增加一个紧密捆绑美国利益的盟友。另一方面,利用远在天边的美国来抗衡近在咫尺的苏联,也是伊朗外交的理想选择。双方一拍即合,伊朗的核项目在美国的支持下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1957年3月,伊朗与美国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与此同时,美国还拉上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共同参与伊朗核建设,计划在2000年之前为伊朗建成23座核电站。德国西门子的一个子公司负责修建具有标志意义的伊朗首座核电站——为德黑兰等中心城市供电的布什尔(Bushehr)核电站;法国法玛通公司(Framatome)承建的伊朗核反应堆也在70年代开工。美国则主要负责提供核原料和技术支持,麻省理工学院与伊朗政府签订了核能人才培养协议。1967年,伊朗官方机构德黑兰核能研究中心成立,美国先期提供了5.545千克浓缩铀、112克钚用于启动研发项目。伊朗核项目的招聘广告遍布西方媒体,这个资金充裕、政局稳定(巴列维政权获得西方国家的一致支持)的国家成了检验民用核能经济性的理想试验场。
伊朗发展核能有一个绕不开的悖论:该国的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倘若以“传统能源不够用”为由发展核电,实在是说不过去。于是伊朗与美国政府共同打起了“全球一体化”的大旗,巴列维国王表示,在全球范围内“石油是稀缺资源”,伊朗不应只考虑自己,把全人类的宝贵资源大量用于本国发电。福特总统的智囊团则在战略报告中写道:“帮助伊朗发展核电,不仅能满足伊朗经济发展的要求,还能释放其石油产量以供出口。”
在美国的核能输出版图中,民用与军事领域遵循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在军事方面,美国在北约内部实行“核共享”(Nuclear sharing)策略,向其他北约国家提供核武器以及必要的维护使用技术,以消除这些国家以安全为由发展核武器的动机。迄今为止,荷兰、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军队都部署了来自美国的核武器。在民用领域,美国则主要通过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核心的规则体系来实现控制。具体来说,就是把发展核能的国家分为“原料提供国”和“技术使用国”,仅让一部分国家掌握浓缩铀和钚的生产,其他国家必须进口原料,无法建立完整的核产业链。
伊朗显然属于“使用国”范畴。发展核能伊始,伊朗就签订了大部分美国主导的相关国际条约,包括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TBT)、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1974年,伊朗颁布《核能法》,详细规定了核能在能源、工业、农业、医疗等领域的和平用途。在购买核原料方面,伊朗向法国兴建的Eurodif反应堆项目提供11.8亿美元贷款,换取该反应堆浓缩铀产量的10%。这些行动完全符合美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构想。当时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伊朗核工业会变成这一构想的反例。
很多人认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核工业的变化,证明美国的和平核能框架只是幻象。然而,并不是“伊斯兰革命”撼动了艾森豪威尔构想的合理性。事实上,美国人主导的核不扩散体系存在先天不足,“限制军用”与“推广民用”之间的防火墙效果十分有限,有些失效是规则不完善导致,有些则是核大国有意为之。
失效的“防火墙”
【在伊朗“是否试图发展核武器”这个最基本问题上,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看法】
美国所倡导推动的核能和平利用体系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核不扩散条约》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限制核能的军事发展,促进核能的民用发展。这就要求在军用和民用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之为“保卫”(safeguard)机制。从历史的角度衡量,“限制核武器”以及“构建防火墙”这两个任务都难言成功。
从美苏先后成功核爆、开始商讨禁核协议到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正式签署的十几年中,三个国家搭上了“拥有核武器国家”(NWS)的末班车:英国(1952年)、法国(1960年)和中国(1964年)。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著名演讲即便没有进一步激发其他国家的拥核野心,至少也没有像它表面所说的那样,起到“核能和平化”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自身也没有展现出削减核武的诚意,艾森豪威尔上任时美国有1000件核武器,他离任时这个数字激增到2.2万件。
对于《核不扩散条约》的189个缔约国而言,该国际框架或许可以起到限制核武的作用。但没有签署这一条约的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签署后又宣布退出的朝鲜,纷纷成功将核能运用于军事领域,国际社会似乎对此无计可施。
更糟糕的是,即便是在核不扩散框架内,原本预想的“保卫”规则也很难充分有效地实施。首先,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核输出大国逐渐对出口的核燃料失去控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各国对核燃料的去向和使用情况进行严格记录,由于各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一点变得难以执行。例如在越南战争中,南越政权兵败如山倒,美国援建的核反应堆根本无法在被攻占前及时抽出燃料。苏联解体后,核燃料被内部人员私吞转卖的现象也很猖獗。据统计,冷战期间,美国总共向别国提供了约25吨浓缩铀,苏联提供了约11吨,流落民间无法追踪的数量难以估计,全世界现存核燃料及废料(仍可用于制造贫铀弹)总计100吨之多。
由于民用核能对浓缩铀的纯度要求比核武器研发低得多,许多人计划仅向非核武国家提供低纯度浓缩铀,通过这种手段构建防火墙。但在具体实践中,早期民用核反应堆依然需要高纯度浓缩铀才能较好运行,设计使用低纯度浓缩铀的反应堆纷纷遇到效率问题,导致武器级浓缩铀依然被应用于平民设施。1967年,美国帮助伊朗建设实验性核反应堆时,就使用了5.585千克纯度为93%的浓缩铀。1978年,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启动了“减少铀浓缩和实验性反应堆计划” (RERTR),派出技术专家考察各国民用核设施,通过谈判劝说其放弃使用高浓缩铀,转而采用低纯度浓缩铀的替代技术方案。2007年《芝加哥论坛报》采访了该项目当年的负责人特拉维利(Armando Travelli),后者提到一件耐人寻味的往事,一位美国情报官员找到他,询问道:“你们是不是只能考察美国提供燃料的核项目并替换浓缩铀,而无法要求苏联人援建的反应堆这样做?”该计划只进行了几年,在政治、技术和资金上都遇到重重阻力,80年代初就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提供支持而被迫停止。提起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针措施,政治领袖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执行起来,谁也不愿在战略对手之前采取行动。
《核不扩散条约》“保卫”规则的另一个难题,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工作长期处于“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状态,他们只能进入目标国家自愿提供的设施内进行检查。这导致很多“越界”核项目就在检查人员的眼皮底下进行。直到1993年,国际社会才开始商议《核不扩散条约》的附加议定书,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大的权力,使其有权在短暂通知后强行进入可疑场所检查。
巴列维政权没有等到《核不扩散条约》完善的那一天,这位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末代君主在施政方针上过度西化,激起了伊朗传统社会的强烈反弹,在人民眼中他和昔日英国和沙俄的殖民者并无实质区别,无法带领国家实现真正的独立自强。在二战后席卷全球的去殖民化和民族独立浪潮中,伊朗的宗教势力逐渐崛起。1979年伊斯兰革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朗在被世俗政权统治多年后,突然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国家。西方世界震惊之余,也陷入了恐慌,伊朗核工业拥有丰富的技术和人才,如果成功研制出核武器,将彻底改变海湾地区的势力格局。然而,在伊朗“是否试图发展核武器”这个最基本问题上,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看法。在历经战争和制裁之后,伊朗依然留在《核不扩散条约》中,并没有像朝鲜那样断然退出。与贸然进行核武研发(进而招致西方直接打击)相比,伊朗更想在美国建立的框架内“合法”获得发展核工业的权利,与之前不同的是,伊朗希望能够进入全球核产业链的上游,成为“原料提供国”的一员。
“后革命时代”的伊朗核工业
【铀浓缩成了伊朗核问题谈判的焦点,但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西方几乎一口咬定伊朗“即将研制出核武器”。例如1984年西德情报部门“泄露”给媒体的报告显示,他们认为伊朗在两年内就可以借助巴基斯坦提供的燃料研发出核武器;美国国会的一个小组则认为,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还有7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推断都是错误的。
当时西方对伊朗的核能力进行过高估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两个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印度和以色列在几年内先后成功研制出核武器(印度于1974年,以色列始终未公开承认,但据信是在1979年),令国际社会对核武问题高度紧张。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十分亲密,1974年印度核武试验成功后,中情局发布报告认为,伊朗“毫无疑问”将与巴基斯坦合作进行核武研发,以对抗印度的威胁。第二,西方世界对伊朗1979年革命的恐惧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伊朗当时的“去西方文化”运动和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也加剧了西方对伊朗的妖魔化宣传。1980年,伊拉克在美国和苏联的共同支持下进攻伊朗,打响了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此时令国际社会相信伊朗“即将研制出核武器”,无疑是诠释战争正当性的好借口。巧合的是,23年后,美国又以同样的理由向伊拉克发起进攻,时代变迁,大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却都大同小异。
伊朗没有像西方专家预测的那样,在短时间内研发出核武器,但该国核工业的发展脚步始终没有停止。按照伊朗人自己的描述,他们其实“被迫”从单纯的核燃料使用国变成了生产国。1979年革命后,西方企业切断了与伊朗核工业的全部合作,布什尔核电站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80%,只能暂时搁置。更重要的是,伊朗失去了上游的核原料来源,与法国Eurodif反应堆签订的浓缩铀供应协议从未履行,在非洲收购铀矿的行动也遭到西方阻挠。这使伊朗自行发展铀浓缩技术具备了充分的理由。《核不扩散条约》并不禁止非核武国家从事浓缩铀生产,198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甚至提出了“帮助伊朗建设铀浓缩工厂”的计划,只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实施。
整个80年代,伊朗被拖入跟伊拉克的战争中,许多核设施被战火损毁。战争结束后,伊朗立刻重拾中断的国际民用核能领域合作,只不过这一次的合作方变成了苏联和中国。1990年,苏联同意接手德国人留下的“烂尾工程”布什尔核电站,建设工作后来由俄罗斯继承,并在2008年完工。伊朗的铀浓缩技术也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2003年伊朗官方正式宣布正在建设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系统;2006年,伊朗宣布成功生产出反应堆可使用级别(3.5%)的浓缩铀;2012年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已经具备将浓缩铀提纯到20%的能力。
铀浓缩成了伊朗核问题谈判的焦点,但这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美国断言发展铀浓缩技术代表了伊朗具有研发核武器的意图。但民用核能与核武器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超过半个世纪的“保卫”工作中,始终难有定论。事实上,该机构在2003年曾发布报告认为:虽然伊朗隐瞒了部分核项目,但“没有证据显示伊朗存在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公开数据中,列出了全球的43家铀浓缩工厂,其中阿根廷一家、澳大利亚一家(已停止运营)、巴西六家(三家运营中)、中国两家、法国三家(一家运营中)、德国三家(两家运营中)、日本六家(一家运营中)、荷兰一家、巴基斯坦一家、俄罗斯四家、南非三家(全部已关闭)、英国两家(一家运营中)、美国十家(两家运营中)。除去五大“签约”拥有核武器国家和未签约的巴基斯坦外,尚有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欧洲的德国和荷兰、亚洲的日本等国在进行浓缩铀生产,是否这些国家全部“具有研发核武器的意图”?很多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一次采取了“双重标准”。
政治与外交的复杂维度
【伊朗特殊的地缘位置一如既往,它依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际势力争取的对象】
伊朗核问题在联合国多次表决和国际社会多年斡旋后依然久拖未决,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内因来看,伊朗赋予核工业极高的战略意义,对于维护国内稳定和树立国际威信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该国不可能轻易放弃已有的技术进展。伊朗的核战略由宗教最高领袖决定,不因总统更迭而改变。每当铀浓缩技术取得进展,都由总统亲自发表讲话,俨然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伊朗也为自己发展核工业找到了看上去合理的逻辑:首先依然是“石油资源有限论”,按照伊朗石油部长2005年的说法,该国的石油将在90年内耗完,发展包括核能在内的新能源是当务之急。其次是对“铀浓缩权力”的捍卫,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曾表示,将核燃料生产和使用隔离开,浓缩铀生产国借垄断攫取巨额利润,是对下游用核国家的一种“压迫”。“每个国家都应获得生产浓缩铀的公平权利。”内贾德在一次激情澎湃的讲话中表示,伊朗将勇敢地充当先驱,带领被核大国压迫的国家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
另一方面,伊朗问题在美国政坛也十分敏感。60、70年代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开明社会”进行了大量的正面宣传,使其1979年革命后对西方文明的“背叛”更加不可原谅,导致舆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妖魔化伊朗的倾向。当美国政府试图与伊朗缓和关系时,总是遭遇巨大的舆论压力。1986年因美国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而引发的“伊朗门”事件,几乎导致里根下台;而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则得到了美国舆论的普遍支持;不久前BBC在美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5%的美国人对伊朗怀有好感。
现在伊朗核问题谈判来之不易的进展,表面上是“温和派”鲁哈尼2013年8月就任伊朗总统后的“峰回路转”,实际上早在2013年初,奥巴马特使就对德黑兰进行了“绝密造访”,美国政府至今不愿将那次密谈的细节公之于众。虽然跟60、70年代相比,伊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一如既往。它依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大国际势力争取的对象,加上了核能因素后,围绕伊朗进行的战略博弈无疑将更加复杂。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中国核电信息网拥有管理留言的一切权利。
您在中国核电信息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中国核电信息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中国核电信息网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用意见反馈向网站管理员反映。
 其他最新 供应信息
其他最新 供应信息
©2006-2028 中国核电信息网 版权所有 服务邮箱:chinahedian@163.com 电话:13263307125 QQ:526298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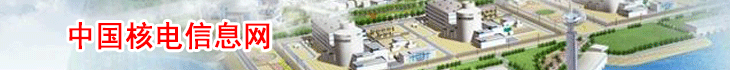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